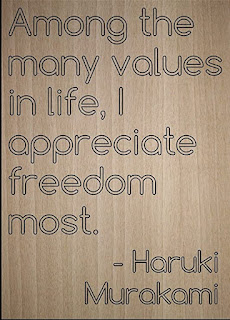對我來説,村上春樹既叫人著迷,也叫人迷惑。他善於營造氛圍,翻開他的書,讀者很快就代入書中的世界,與虛擬的人物一同呼吸,一同經歷喜樂和憂愁。加上他的情節扣人心弦,往往讓我不期然的翻了一頁又一頁,三大冊的《1Q84》,我不到兩個星期就看完了。然而,對於製造「空氣蛹」的little people、「貓之村」等超現實情節,卻是丈八金剛摸不著頭腦,只好不求甚解。我相信這書是有深意的,不能視作通俗的驚悚小説。
其次是村上的主題,楊照認爲,村上的作品雖然千變萬化,但數十年來都是固執不變地圍繞著三個的主題,分別是:
人與自由的關係,取得自由之後要如何運用自由,這不是件簡單的事,很多時候甚至是件恐怖的事。
人與人之間的疏離。人活在一個我們無法追究,永遠莫名其妙的世界裏,這個時間迫使我們採取一種疏離的,憊懶的生存態度或生存策略。
雙重,乃至多重世界的並置,拼貼,而且用這種手法來彰顯我們所存在的具體世界。
接著,楊照以村上的多部作品為例子,反復論述這些主題的運用。由於篇幅太長,這裏不便引述。我只是留意到,書中沒有明確指出,這三項主題之間的相互關係。我嘗試這樣理解,連接這些主題的共同背景,是現代社會。有別於充滿規限束搏的傳統社會,現代人享有比過去任何年代更大的自由,但自由越大,困惑也越大,選擇者要負責選擇帶來的後果,不能埋怨傳統。其次,各人有不同的選擇,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就因而擴大,越走越遠,越來越難找到共通的關懷和認同,人與人之間變得疏離,冷漠,用文學的手法來形容,就恍如大家活在平行時空,活在重叠的世界。這是現代人的可悲。
了解這三大主題,其實只是掌握了入門的要訣而已,因爲村上的小説的背後包含很多典故,例如《海邊的卡夫卡》,除了卡夫卡的一篇少為人知的短篇小説,還有古希臘悲劇的典故,村上透過他的創作,對這些經典作出新的詮釋。另外,也有些典故是來自村上小説之間的 “互文”,即是說,人物和情節互相指涉。以牛河為例,原來這位奇醜無比,到處惹人討厭的人物,在《發條鳥年代紀》和《1Q84》都出現,我沒有看過前者,所以錯失了某些訊息。楊照指出,模仿村上的作家,只知道模仿他的表面風格,但大概他們不知曉這些典故,所以只有形似,得不到村上的神髓,此乃東施效顰。他因此不惜花了大量篇幅,講述這些經典作品的内容,並指出這些作品和村上小説的關係。另外,他又把村上的作品對照大江健三郎,因爲兩人都是日本文學圈的局外人,彼此關注的問題也相近。看了他的分析,我才恍然,難怪我看不懂。
綜合而言,楊照的評論讓我有點茅塞頓開之感,因爲這書給我有用的坐標,以理解村上在小説情節背後所要傳達的訊息。但我要提醒自己,他的評論可以作爲參考,但不要視爲絕對,所謂文無達詁,上乘的文學作品,不能只有一種解讀方法,每一位讀者都應該有自己的看法。如果我們拿著某評論家的框架,視爲金科玉律,把村上的作品對號入座,不但失去閲讀的意義,也失去閲讀的樂趣。